服务热线:
010-68025875
周一至周五 8:30-16:30
地址: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22号1幢8层
微信客服:hongse191919

1
2016年,四十四岁,不惑之年。
欲买一款重疾险,以防不测。因保险流程需要,多年来对感冒都一直不曾“感冒”的我,破天荒去做了一次“阉割版”体检。
之所以说是“阉割版”体检,是因为只检测了诸如血压、血糖、血脂等基本指标;老实说,不热衷体检的我,那时候还并不知道什么“美年大健康”,以及什么动辄上万的VIP体检服务等概念。
那是个民营小医院,离家很近,收费也便宜,平常主要接待些农村来的病人,又或者老年人,生意倒也不愠不火的。
这家医院的老板,在某个酒局上我曾见过。中等身材,戴着眼镜,憨厚的措辞中,闪烁着商人特有的精明与狡黠。正餐结束转场时,他悄悄塞给领导两条香烟,被领导转手做了人情,当场分发给在座的其他各位,弄得他很尴尬,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。
医院扎营在一个老旧小区旁,五层楼高,外立面墙砖因年久失修,局部有脱落现象,露出浅灰色的墙面,东一块西一块的,并不规则,远远看去,犹如癞子的头皮,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斑驳陆离。
稍微靠近医院门口,便能闻到浓郁刺鼻的84消毒液味道;医院大厅里安放着几把木质长椅,椅子的边沿已经被磨得油光发亮;锈迹斑斑的铸铁底座,则清晰而明了地昭示着医院的历史。一些病人或坐在木椅上输着液,两眼茫然;或不停翻看手机,偶尔也咧嘴发出开心的笑声。
前台接待的几个小姑娘,十八九岁年纪,个个都抖着一股子机灵劲;她们脸上的笑容,质朴而丰盈,足以在寒冷的冬天,温暖整个世界。
那天我去体检的时候,大概是早上八点过几分,才上班,并没有什么病人。
一个卫校实习的护士,给我测的血压;用的是汞柱式血压计,她温柔而细致地绑好,带上听筒,倒也有模有样的。
第一遍检测结束后,她没说结果,只自个儿嘟哝说:
“昨天才用了的吔,咋今天就坏了呢?”
于是又换来一个血压仪,又测了一次,照样没告诉我结果,她开始询问:
“平常头晕不?”
“不晕!”
“抽烟喝酒不?”
“抽!喝!”
“有其他什么异常没?”
“没有!”
她再次拿来一个全新的电子血压仪,又测了一次,然后对我说:
“你等等,我去找医生来。”
她口中所谓的医生,其实也是一个护士,只是年长了些而已。年长的护士了解情况后,对我说:
“你可能患有非常严重的高血压,但我们不确定,保险起见,建议你去大医院复查一下。”
“我好好的,啥症状没有啊!昨晚还在喝酒呢,怎么可能有高血压?会不会搞错了哟?”我满眼狐疑地说
年长的护士很同情地看了我一眼,边不紧不慢收拾血压仪,边说:
“你自己决定吧!毕竟身体是你自己的。”
“当然,我们只是建议!”末了她又画蛇添足地补充说了一句。
连个血压也查不准,还能叫医院吗?
走出福鑫医院时,我暗暗发誓,再也不会来这种小医院了,简直是浪费表情。

2
一般情况下,我是不愿意来人民医院的,因为它生意确实太好了。举目望去,满眼皆是人头攒动;患者来来往往,其人流并不亚于周末的王府井商场。
我提前三天预约,才背上那个巴掌大小的“24小时血压动态监测仪”,当它被取出来时,还带着我的些许余温,但这种余温却让我感到极度的不适;因为我不知它被多少人背过,也不知道还会有多少人来背它。我甚至还有点担心上一个人用完后,会不会作消毒处理?
毕竟,科室里这玩意数量少,使用频率又很高,医生们一旦忙起来,顾不顾得上消毒,是很难说的。
接诊我的是一位胖胖的女医生,三十多岁,齐耳短发;白大褂套在外面,全部敞着,露出里面的深灰色外衣。她机械地接过我手中的监测仪,用专用数据线连上电脑,大致看了眼电脑屏幕,便熟练地敲了回车键,接着打印机便开始疯狂地输出。二十多页监测记录旋即便次第而出,但并不断开,藕断丝连般在地上一层一层往上堆叠,直到最后一页欣然做了封面。
那期间胖医生和我都没有说话,只有那“嗒嗒嗒”的光敏纸打印声,有节奏地响着,宛如法庭上公诉人铿锵有力的起诉;而我,则更像是一个悲催的嫌疑犯,心神不宁地等待着法官的最后判决。
胖医生突然问了一句:
“家族里有高血压病史没有?”
我回答说:“父母兄弟姐妹都没有,但再往上,就不知道了!”
“监测报告显示,24小时均值,低压138,高压176,属于原发性高血压,三级!”
胖医生皱着眉头看完监测报告,用不容置疑的语气下了断语。尔后,她也并不询问我的意见,便直接给出了她心目中最合理的处置办法。
她说:
“从今天起,立刻、马上,降压药,吃起走!”
“注意生活和饮食的规律性,多锻炼,少吃肥肉,少熬夜!”
“哦对了,烟酒,必须全戒了!”
最后一句话,她说得斩钉截铁,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。我从她的语气中,暗自揣度,胖医生的老公,应该也是我的同道中人。但当时脑袋嗡嗡的,大脑一片空白,胖医生还说了些什么,我已不记得了。只记得她递处方单给我的时候,我没接住,处方单飘飘荡荡,翻了无数个滚,掉在了远处的垃圾桶盖上。
买个保险,做个体检,居然折腾出了这么个结果,实在也是哭笑不得。
“真有这么严重吗?咋啥感觉也没有呢。”我还是不甘心,弱弱地问。
“等哪天血管突然爆裂了,你就有感觉了!”胖医生没好气地回怼了一句,我的那个难受啊,如同喝水时被噎住了一样,说不出的滋味。
万般皆苦,唯有自渡,没有谁会在乎你的情绪。
广播里又冷静地响起叫号声:“第38号,请到五诊室就诊!”
见胖医生下了逐客令,我只好捡起处方单,吹了吹上面的灰尘,茫然告退。
就诊显示屏上,患者的名字不停翻滚,像极了电视广告里,那些洒落的药丸。它们泛着精光,裹着糖衣,带着微笑。

3
我转身来到了门诊刘主任的办公室。
刘主任是一个朋友的朋友,在一起喝过几次酒,一来二去便熟识了。
房门虚掩着,我推门进去,只见他正翘着二郎腿在抽烟。袅袅烟雾从门缝中逃逸,与右侧面的窗口形成了理所当然的对流。
桌上摆着包“细支荷花”,旁边还有一个仿“ZIPPO”燃油打火机。
“咋了,老弟,愁眉苦脸的?”他问到。
我把监测报告递给他,说,麻烦帮我看看这个报告呐。
他快速扫了几眼,说:高血压,有点严重哦!
“好严重?”我急切地问,声音有些打颤。
他甩给我一支烟,又把打火机递给我,笑着说:来来来,莫急,莫急,抽支烟压压惊!
以往吸烟,轻轻来一口,然后烟入喉三分之二处,打个转(相当于出口转内销的商品,在公海上转一圈再回来),再悠悠呼出,很少入肺。呼出时,要么从鼻翼两侧的孔洞缓缓而出,如化工厂的烟囱冒着白烟那般壮观;要么嘴唇微启,让烟漫不经心地从嘴角斜溜出;兴致来时,也喜欢卷起嘴唇和舌头,吐出几个连绵荡漾开去的烟圈炫酷。
这天,我完全没了往昔的优雅与从容,点上香烟,猛地深吸了好几口。每一口烟,都顺着食道,直奔腹腔而去;尼古丁终于在关键的时候,发挥了关键的作用。我原本焦躁的心情,慢慢缓解,趋于平和,保持住了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应有的处变不惊与淡薄。
“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,坚持吃药控制就可以了!”刘主任不紧不慢地说,“你有什么好害怕的呀?”
“如果不吃药呢?”,我问。
“不吃药有血管爆裂的风险,但也不一定,这也有个体差异。”
“不过,又何必拿生命去冒这个险呢”
“烟酒都必须要戒了吗?”我又问了一个我很关心的问题。
刘主任呵呵一笑,说:
“医生的话,肯定没错的,但是——
世间万事万物,看你如何去想;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,我的观点未必就适合你,所以,决定权还是在你自己手中。”
紧接着,他又补充了一句:
“其实,我也是高血压,现在天天吃药呢。”
刘主任的高论,让我豁然开朗,也如释重负。
我知道,站在医生的角度,他这样说,有些叛经离道了;但作为朋友,他这么说,其实才是最真实的表达。
而于我,胖医生宣判那一刻,其实就已经默认了事实的真相;之所以又辗转到刘主任这里来,不过是心存侥幸,或者是不愿意接受罢了。
人生很多时候,都是无助的。
“你厉害!像你致敬!”我也甩给刘主任一支香烟,“啪”地点燃打火机。
幽蓝的火焰,一跳一跳的,似鬼魅的眼神,在无声地嘲笑着我的懦弱与无能。

4
烟与酒,都是故事的佐料与道具。
那间房子是两层楼的木质结构,人在上面走动,一颤一颤的,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声响,如同过吊桥,我总担心它会不会塌了下去。
房子是同学鑫的姐姐分得的单身宿舍,被鑫强要过来的;鑫的姐姐不苟言笑,端庄威严,天生就是当老师的料。那时我和鑫都十分怕她。很多年后,同学聚会,鑫因喝酒后,骑电瓶车出了个小事故,我再次见到了鑫姐;和她对视的时候,我还是一如当年般心虚和慌张。
她朝我轻声埋怨道:“你们这个酒啊,喝喝喝,总有一天要喝出人命!”我既不敢点头,也不敢摇头,只能讪讪地笑着,算是回应。
但她永远也不会知道,正是她的亲弟弟,在她的单身宿舍里,仅用一下午的时间,便教会了我终身受用的两样技能:
酒与麻将。
我们从一张牌一张牌的认识开始,到洗牌手法、砌牌样式、摸牌动作、拿牌顺序,最后到胡牌原理,他教得极其耐心,我也学得特别认真。直到学校晚餐开饭时,我便去打了饭菜回来,只见鑫变戏法一样,又从床下摸出一瓶白酒来,酒盒上赫然印着“文君”两个字;夕阳斜照进来,将酒瓶映得晶莹剔透。
我问他:“咋还有这玩意,哪里来的?”
他说,是一个求他爸办事的人送的,放在他家门口鞋柜旁,他爸没瞧见,早上出门时他藏在夹克衣服里顺出来的。
就着食堂打回来的饭菜,没有任何仪式,他一口,我一口,半小时左右,便硬生生地把那瓶酒给消灭了。
那是我第一次喝酒,却并没有感觉到喝酒的快乐。
最初只觉得舌尖涩涩的,待酒入喉,则火辣辣的刺激,让人浑身燥热,血脉喷张。有好几次,还被呛得眼泪直流。
那个下午,那间木房,那些麻将牌、那瓶酒,以及那个酒盅,还有窗外的残阳,便一直烙在我的记忆中:
真实而荒诞,孤独而深刻。

5
喝酒那时,我还没有学会抽烟。
每当看到父亲吧唧吧唧的抽着土烟,浓烈的烟味呛得他咳嗽不止,我便掩着鼻子,说:
“老汉,这有啥好抽的嘛,闻到都想吐。”
父亲并不回答我,他将烟杆在地上磕几下,倒出几滴烟油,然后用纸擦拭干净,起身走人。
父亲那时是拒绝抽盒装纸烟的,他说抽起来没劲,许是为了节约钱吧;但每次他裹完土烟,地上都会留下一堆烟叶的茎骨,七零八落的,像曝尸荒野的野狗。
我大抵是大一年级时开始抽烟的。
只记得,寒暑假回老家时,我身上也开始揣着烟了。见到乡邻,我也学着那些大人模样,递上一支烟,并有一搭没一搭地寒暄上几句,机械而幼稚地展示着自己所谓的懂事和礼貌。
我也给父亲递烟,但他总是摆摆手,然后掏出自己卷的土烟,吱地划燃火柴。
父母亲那时并不责怪我的抽烟行为;或许他们开明地觉得,我已经长大了,抽烟喝酒,是再正常不过的了。
而乡邻们对我的礼貌与懂事,那自是赞不绝口的;母亲曾无数次自豪地对我说:
村上某某某,常对她说,全村这么多从村里走出去的年轻人,只有你家儿子的香烟,他们每年都能抽上一两支。其他的,都忘了本,坐在小轿车里,都懒得下来。
母亲说的时候,我就笑着开她玩笑:这说明你教子有方嘛。母亲很是受用。
这座丰碑,我一背就是几十年,从未放下。
至今,每每回老家,我都必备两包香烟,从村口开始,看见熟悉或觉得熟悉的人,便下车,大方地发烟,偶尔也递上打火机,点燃,陪抽几口,然后千篇一律地说:
“先忙,先忙,空了再聊,空了再聊!”
汽车的尾气和着香烟的烟雾,便一直盘旋在乡村公路上,久久不散;有时,也随风飘到正坐在门前闲聊的几个婆婆的鼻前,她们厌恶地用手扇扇,眉头皱得像拧麻花。
淳朴的乡邻们也许并不在乎我那一支香烟和虚假的客套说辞,但我确实很在乎。因为我在乎母亲的感受,也在乎自己在乡邻心目中的人设。
酒,常喝的是故事;而烟,抽的则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人情世故。

6
关于戒与不戒?我只纠结了三天,最后向科学让步,决定二选一,戒。
至于是戒烟,还是戒酒,我纠结了至少一个月。毕竟都是最爱,取舍都会心痛。
世人贪心,鱼和熊掌,都想要,但天下并没有这样的好事。
那天早上,感冒了,咳嗽不止,五脏六腑似乎都要咳出来。于是,我翻身起床,将未抽完的“荷花”连同价值一元的打火机,像投三分球一样,轻轻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,稳稳地扔进了垃圾桶。
金属质感的垃圾桶,轻轻晃了晃,尔后便归于平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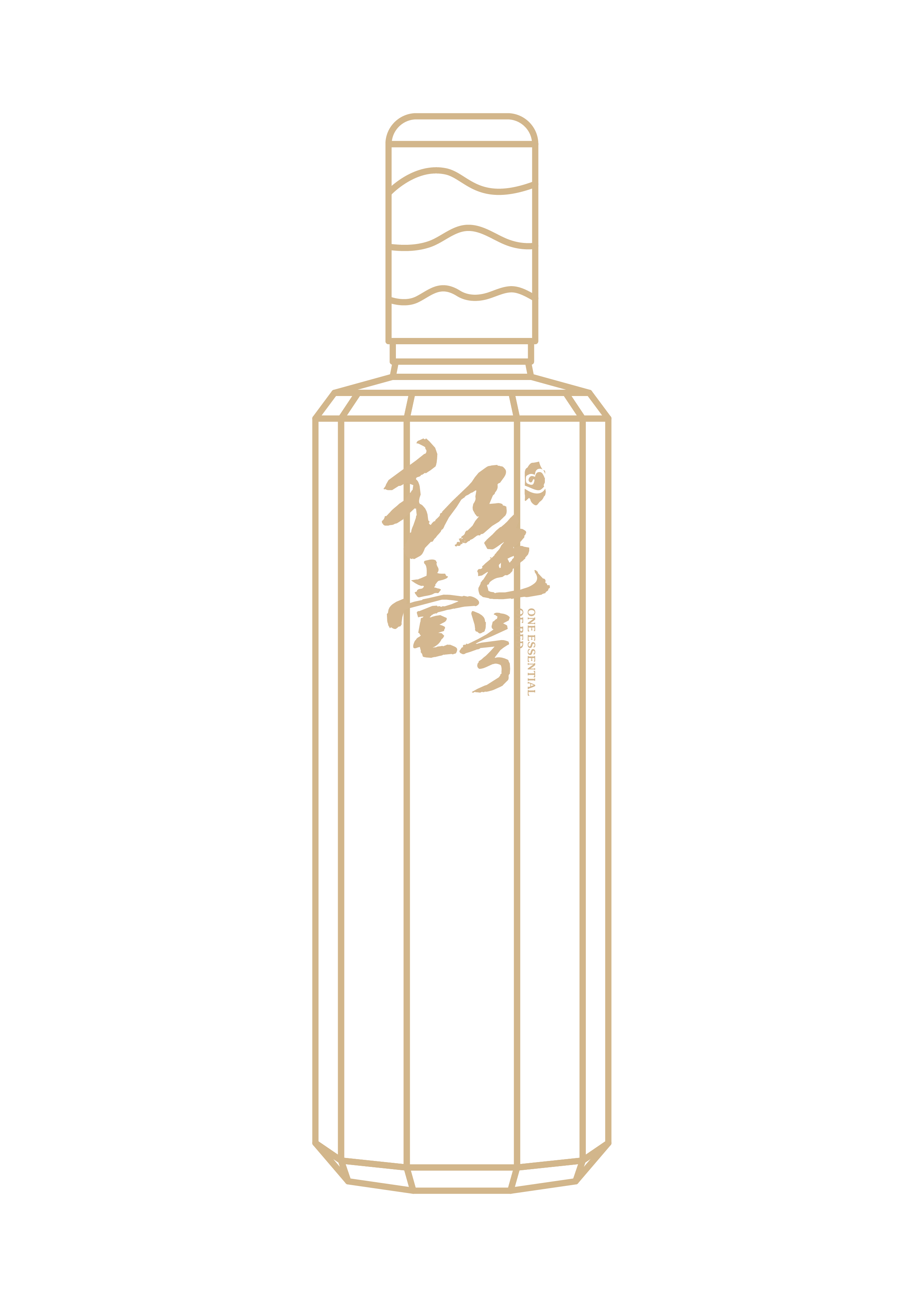
今天是2025年4月26日,
乙巳蛇年农历三月廿九,
世界知识产权日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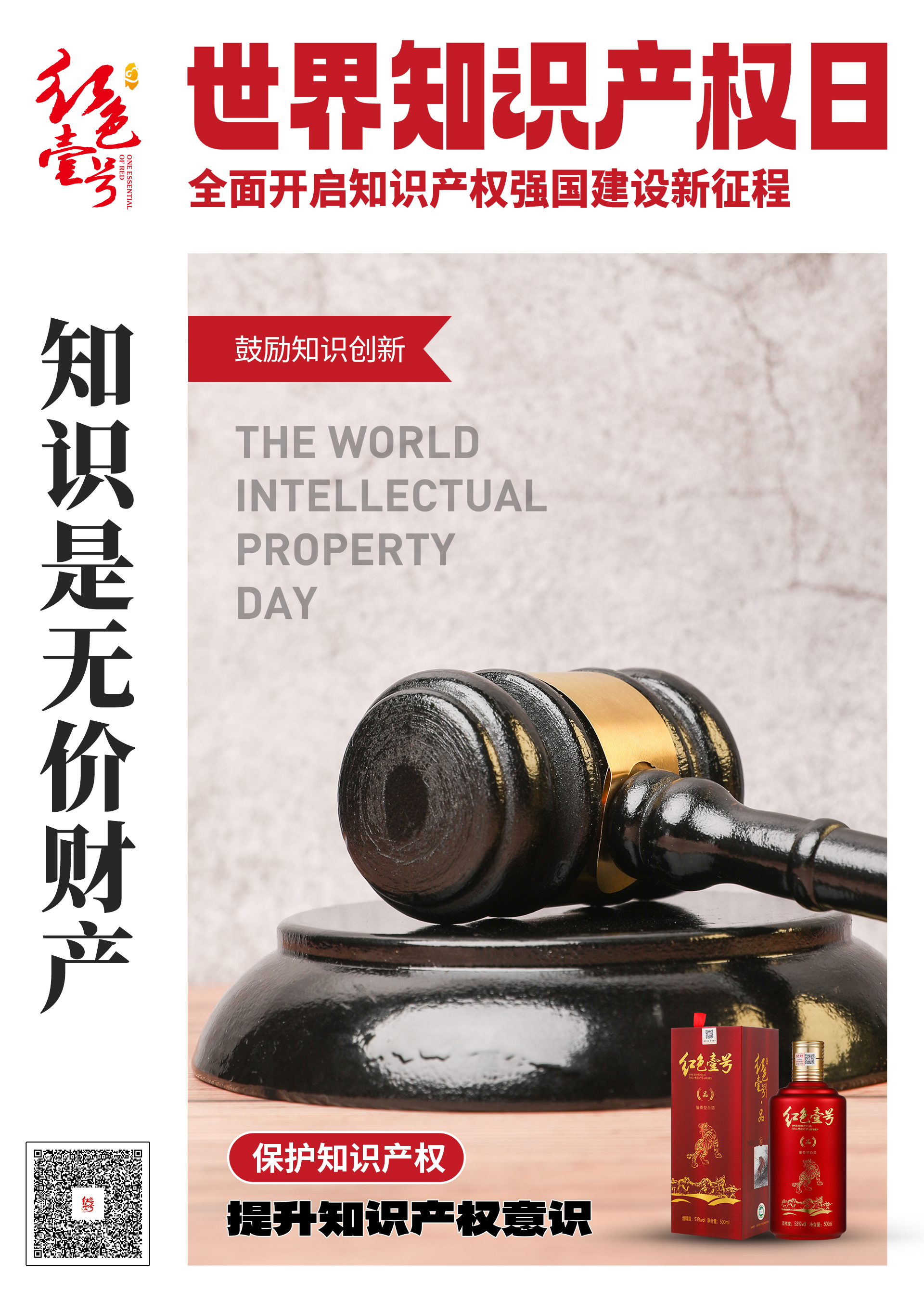
不要活在过去,
或只是为了未来而活。
现在很重要,
当下很重要,
即使它只是一块不起眼的砖头,
却能垫起你明天的一段高度。
不要说真爱难寻,
而将爱排除在你的生活之外,
接受爱的最快方式是给予,
感受爱的最好方式是简单,
维持爱的最有效方式是包容。
不要挥霍时间和话语,
这两样东西都是无法收回的。
任何不切实际的东西,
都是痛苦之源,
痛苦源于执着,
努力过好每一天,
培养出世间的智慧,
我们的生活自然充满阳光。
——加措活佛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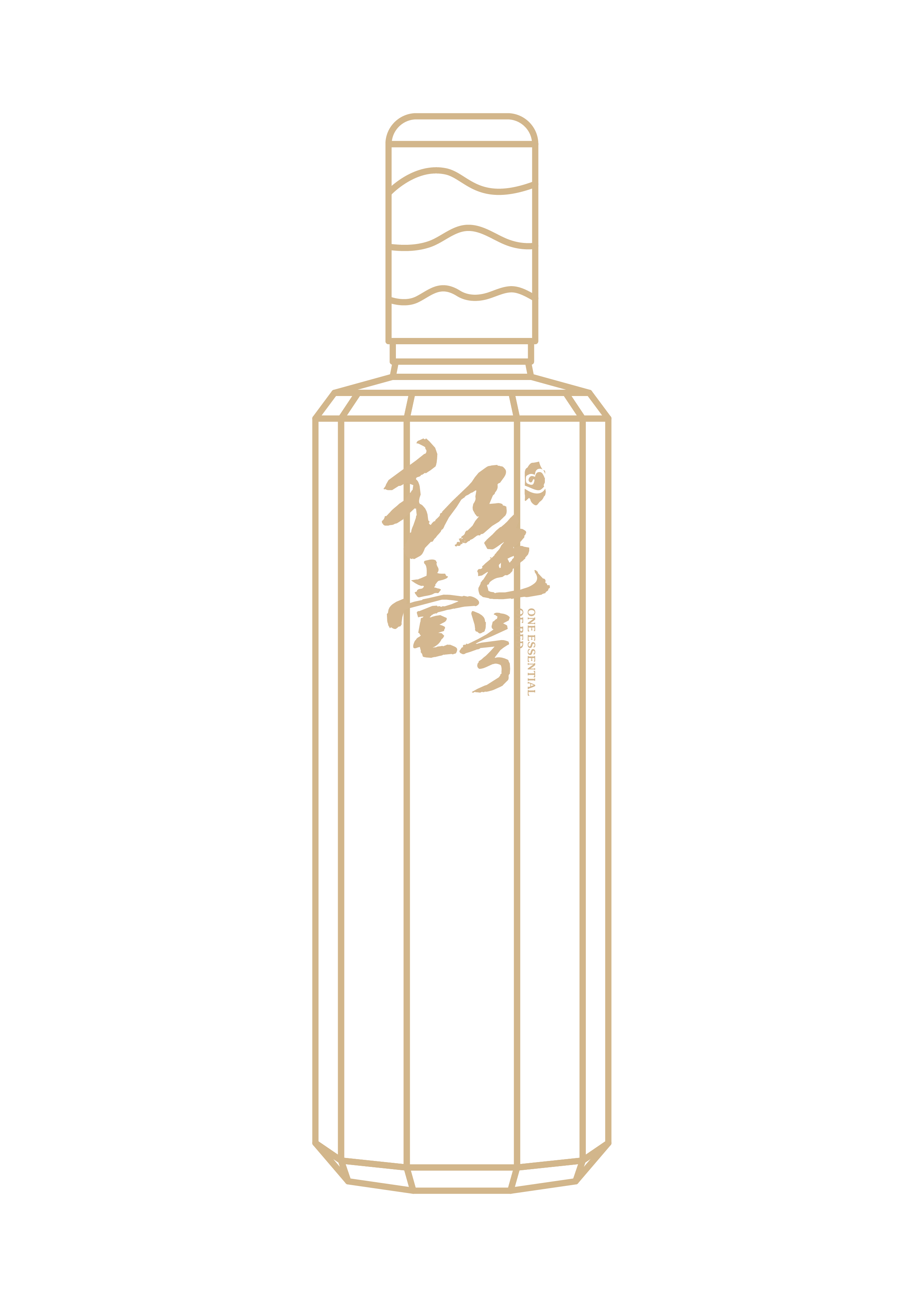
喝红色壹号,展家国情怀!
一号人物,喝红朝壹号!
更多酒文化和人文文化请关注“红色壹号酒业”官方微博和公众号。
